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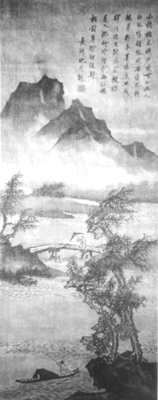
曾在中央電視臺藝術品投資欄目春節賽寶大會中被評為金獎的一幅南宋蘇顯祖款的《風雨歸舟圖》,又帶著諸多鑒定界人士確定其為宋代真跡的題款,出現在北京的某拍賣會上。難道它真是一幅宋代的古畫,穿越了千年的風雨、歸向家園的孤舟嗎?
從鑒定人士的題跋中,看到鑒定人為蘇氏真跡所鑒定的依據是:
畫史上載“蘇顯祖為南宋浙江錢塘人,寧宗嘉定年間的畫院待詔,工山水、人物,時與馬遠、夏圭齊名,筆墨相近,其作品世所罕見。”此畫從筆墨畫法上與馬、夏相近,又有“蘇顯祖”三字隸書款,與畫史所載無異,應為依據之一;
《風雨歸舟圖》上有明代沈周題詩,沈為明代集書畫鑒藏于一身的大家,眼力很高,不會看錯,應為依據之二;
畫用南宋細絹,應為依據之三。
事實上,世間沒有一幅南宋蘇顯祖繪畫真跡存世,這就使我們失去了鑒定中最重要的可比性。人們對蘇顯祖的認識,只停留在畫史中的寥寥數語上,僅憑“蘇顯祖”三字隸書款,就認定《風雨歸舟圖》(圖一)為真跡,未免輕率。
細觀此幅《風雨歸舟圖》,筆墨畫法低劣,與馬、夏之作有天壤之別,沈周題詩明顯是偽作,唯一與鑒定蘇顯祖真跡有關的僅是畫右下角的“蘇顯祖”三字款。
兩宋繪畫水平是中國古代繪畫發展史中的一座高峰,其水平之高,令后世難以企及。這也為以后歷代作偽者豎起了一道高高的屏障,想要超越它,自身必須有很高的書畫功力。事實上,宋元兩個時期繪畫呈現出的鮮明個性和開宗立派的筆墨語言,在之后的數百年間,始終處于無可替代的領先地位。不用說一般的作偽者,即便是著名畫家也未脫其窠臼,鮮見創新之舉。
我們今天能看到的宋元繪畫作品中,無論是主題思想、章法構圖、還是筆墨所表現出的語言等,都是十分優秀的。那么,蘇顯祖作為南宋宮廷畫院待詔,其繪畫水平應該是與馬、夏不相上下的。南宋蘇顯祖繪畫作品除了此幅《風雨歸舟圖》之外,今天的人們是一無所見。那么,僅憑《風雨歸舟圖》上“蘇顯祖”三字,無視畫中其他因素的存在,顯然是武斷和主觀的。
畫史中記載蘇顯祖為南宋畫院待詔,工山水、人物,時與馬遠、夏圭齊名,筆墨相近,作品罕見。我們在判定蘇顯祖繪畫作品時,至少要遵循以下幾點:
蘇顯祖的山水、人物繪畫作品的整體風格、構圖布局、筆墨特點與馬、夏十分相近,也可以說,從繪畫水平方面而言,三人應在水平上是十分接近的;
蘇顯祖為南宋畫院待詔,從現存的作品中看,兩宋畫院中有待詔稱號者不少,但未發現一例是徒有虛名的;
蘇顯祖工山水、人物,說明了其繪畫才能是較全面的,縱觀宋元時期工人物的畫家,其筆下的線條公里往往使后人難以逾越的。
所以,宋元時期的著名畫家、甚至是壁畫中的無名畫家,他們的作品,筆墨水平都是極高的。當我們再來仔細審視這幅《風雨歸舟圖》時,就會感到整幅畫的水平遠非與蘇顯祖齊名的馬、夏作品可比,就是與馬、夏他們的弟子作品相比,也是不夠格的。畫中空闊的地方有大面積的水浪起伏,系用淡墨細線勾出,單筆勾線及勾線之間的組合無變化,更像是一個初學者所為,觀者可參見與蘇顯祖齊名的馬遠繪十二幅《水圖》,既可明白宋畫之精致。畫中山水分近、中、遠三景,分別用水、云相隔,山石多用小斧劈皴法,雖近、中、遠三景峰巒相接,占了畫幅很大部分,僅以粗筆勾勒山石輪廓后,略加皴擦,復以較濃的墨渲染并在畫中上部云靄間以淡墨染出風雨襲來的景色。畫的右下角為坡石,粗筆重墨勾出輪廓后,復勾皴數筆,以濃、淡兩色墨染之,用筆不夠勁健,此處作者用復染之墨色,恰隱其筆功之不足。石上有樹三,畫作頂風冒雨狀,樹干前傾而樹葉后掠,一枯兩茂,唯高峻之枯樹枝干所用鹿角畫法,用筆生疏,枝部疊壓零亂。旁生一樹,點葉之法更像竹葉,無宋人之風,一夾葉矮樹穿插其間,枝與夾葉勾勒零亂無章。樹后橋左兩樹,形呆筆滯,樹枝幾無鹿角之態,狀如韭葉,其中近橋之曲樹,樹干勾勒用筆敗劣,行筆轉折多生圭角,此為畫家之大忌,而這類敗筆普遍出現在山石勾勒和樹木枝干上,暴露出這幅畫的真正作者的水平并不高。遠山以細線勾出輪廓后,僅在正中的山石上用小斧劈皴法,皴出幾筆而大部分山石則被濃墨蓋住,這對于一個作偽者而言,不啻是一個聰明省力的方法,既讓水平不高的觀畫者看后能產生畫面層次“豐富”的效果,又掩蓋了自己線條功力不足的缺陷,但馬、夏之山水,用墨淡而巧,即用墨來豐富畫面的層次,增強變化節奏,又能用白骨法體現用筆之美并展現給大家。我們可以將馬遠的《踏歌行》(圖二)及夏圭的《雪堂客話圖》拿來比較,就會明顯看出他們之間的差距。
《風雨歸舟圖》是一幅筆墨、構圖均比較簡單的作品,尤其是山石畫法的處理上,出現了許多低級的用筆。如果讓作偽者畫一幅像馬遠《踏歌圖》一樣的作品,相信他暴露出的誤差可能更多。
自古以來,中國畫的創作就講求“畫眼”。一幅成功的作品,其“畫眼”必是最精彩的部分,針對蘇顯祖款《風雨歸舟圖》而言,畫中橋上撐傘及舟中持篙之人應為畫眼,成功者即可突出整幅畫的主題,又可活躍氣氛,而失敗者,即如此畫中兩人,人物形象佝僂,勾勒用線全無宋人遒勁流暢之感,勾線行筆中有停滯、猶豫之病,起止筆不連貫,產生了“虛筆”現象,這是一個工人物的著名畫家作品中不該出現的,我們可將這兩個人物和馬遠《踏歌圖》中的人物作一比較,自然就會看出真跡與仿品之間的優劣。
宋人在絹上描繪云霧景色時,云際被渲染得生動而不留痕跡,兩支筆一來一往,盡顯水中筆墨變化,這在宋代諸多山水畫中表現得可謂淋漓盡致。《風雨歸舟圖》中上部的云際處理得比較機械,缺少漸變之奧妙,尤其是加上了自左向右下的斜向的風雨痕跡后,使得整幅畫的韻律更加板滯,絲毫看不到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宋元繪畫中的那種渾厚華滋的精神。所以,這幅蘇顯祖款的《風雨歸舟圖》不論是從構圖還是筆墨功夫等方面來綜合分析,它顯然不符合我們理解的南宋蘇顯祖繪畫作品真跡的條件,也就是說,它是一件繪畫水平不高的贗品。
從它的畫風、筆墨特點等方面來觀察,應是明代晚期到清代中期之間江南一帶仿手所作。從畫面上的題詩來看,似是一首自題詩,但畫風又不似沈周,我們權且認它是件“仿沈”之作,而在其后的傳承和交易中,被某位“高人”認為它并不是一件具有沈風的畫作,因此添上了“蘇顯祖”的三字隸書款以充古畫,但事實是,在其后的歷史中,“蘇顯祖”款的《風雨歸舟圖》并未得到古人的認可,我們從古代留下來的有限文字資料中,也未見到古人對這一“世所罕見的”宋畫有翔實的記載,這反證出古人鑒偽的高明之處和對此畫的否定態度。
古代畫作的傳承,必有記載,尤其是南宋蘇顯祖之作。《風雨歸舟圖》上鮮見宋、元、明、清題跋,僅有明代沈周題詩一首,況書法詩作皆偽。或曰,原作上的題跋,為后世所裁割云云……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想,割了重裱,乃愚人之法,因為證據不存,誰還念你為真?
世間學兩宋繪畫者多矣,技高者不多。明代“院體”為其分水嶺,此蘇顯祖款《風雨歸舟圖》雖受明代畫風影響,但也是僅得其皮毛,偽作者既沒有得到名師指點又未獲觀宋元名畫真跡,率爾操觚,徒成笑柄。